 去看看
去看看


1967年Ashbaugh及其同事首次报道了12例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(ARDS)患者。这些患者表现为严重的呼吸困难、心动过速、发绀及难治性低氧。呼吸生理特点是肺顺应性显著下降,胸部X线表现为弥漫性肺泡渗出。这12例患者中有7例死亡,尸检确证了ARDS特征性的肺脏病理,表现为肺泡上皮细胞表面透明膜形成、弥漫性肺间质炎症,肺间质和肺泡内水肿及出血。
从ARDS概念诞生时至今日已近半个世纪,我们早已清楚地认识到ARDS是一种由多种危险因素诱发的临床综合征(syndrome),而并非是一种单一疾病(disease)。现代医学已取得长足发展,同时ARDS的危险因素也不断增多,例如新型小分子靶向抗肿瘤药物或生物制剂所引起的药物性肺损伤、各种新型病毒导致的重症肺炎(如SARS-CoV、H5N1、H7N9)等。ARDS作为临床最常见的危重症,其救治仍然是最具挑战性的。
从Ashbaugh提出的ARDS最初的诊断雏形至今,ARDS的诊断标准已历经多次变迁。统一ARDS的诊断标准既关系到患者的治疗决策及预后估计,也关系到ARDS相关医学研究的标准化及不同研究的结果之间具有可比性,因此至关重要。毋庸置言,ARDS在任何一个时期的诊断标准实际上并不“标准”,随着对疾病发病机制认识的不断深入,相应的临床诊断标准将获得不断完善。
一、1994年AECC诊断标准
1994年欧美联席会(AECC)颁布的ARDS/ALI的诊断标准包括:①急性起病;②低氧血症:无论PEEP水平高低,PaO2/FiO2≤200mmHg定义为ARDS,PaO2/FiO2≤300mmHg定义为ALI;③正位胸部X线检查呈双肺弥漫性浸润影;④不存在左心衰竭:肺动脉楔压(PAWP)≤18mmHg,或没有左房压升高的证据。在该诊断标准中,首次引入急性肺损伤(ALI)的概念,ARDS是更严重的ALI,应在ALI早期引起足够重视。
1999年9月在昆明召开的全国呼吸衰竭学术研讨会上,我国与会专家也讨论通过了《ALI/ARDS的诊断标准(草案)》。该《诊断标准(草案)》的主要内容基本上与1994年AECC的诊断标准相同(表23-1),但强调了ALI/ARDS的发病必须具备高危因素,包括直接肺损伤因素(严重肺感染、吸入胃内容物、肺挫伤、吸入有毒气体、淹溺及氧中毒等)和间接肺损伤因素(脓毒症、严重非胸部创伤、重症胰腺炎、大量输血、体外循环及DIC等)。强调ARDS的高危因素非常重要,因为在ARDS的治疗原则中,最关键的措施是去除危险因素。如果不能及时去除诱因,即使依靠机械通气、体外膜氧合等先进的高级生命支持技术和设备也难以改善ARDS患者的预后。此外,我国的1999年《诊断标准(草案)》还强调了起病时的症状,即“急性起病,呼吸频数或呼吸窘迫”,保留症状学特点也非常明智,这样会使该诊断标准更接近临床实际、可操作性增强。
表23-1 1994年AECC诊断标准与1999年中国诊断标准的比较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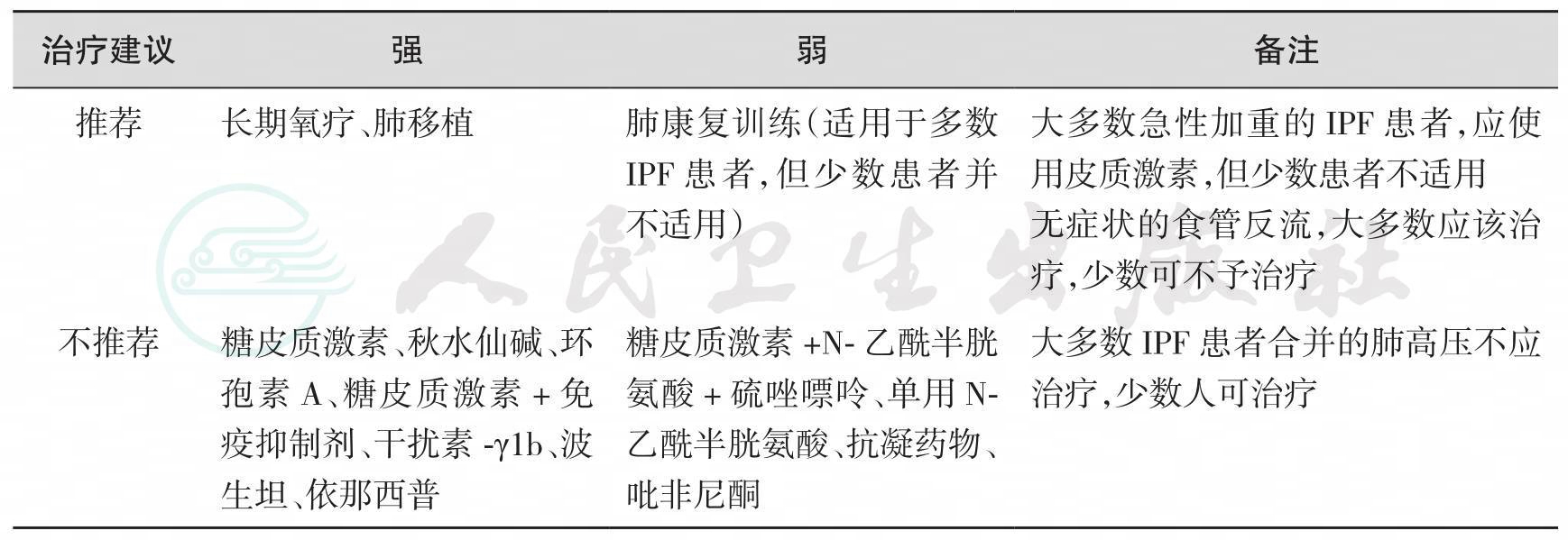
2006年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颁布了中国《ALI/ARDS诊断和治疗指南(2006)》,该指南以循证医学证据为基础,参考了大量国外研究,达成了中国《关于ALI/ARDS的诊断及治疗方面的共识》。该诊治指南分为4大部分,包括:①ALI/ARDS的流行病学;②ALI/ARDS的病理生理和发病机制;③ALI/ARDS的临床特征和诊断;④ALI/ARDS的治疗。在ARDS诊断方面,该指南则完全沿用了1994年《AECC指南》。本指南的最大特点是将国际上近年来关于ARDS治疗的临床研究成果按照文献的研究方法分为5个级别(研究的可靠性由高至低Ⅰ~Ⅴ级)、推荐力度也分为5个等级(推荐等级由高至低:A~E),这样有助于临床医师在ARDS救治实践中积极采纳证据等级高的治疗措施,即有证可循;同时对于证据等级低的治疗措施,可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实施个体化治疗。另一方面,该指南所引用的98篇文献全部为国外研究,由此可见我们亟需开展本土化的ARDS临床研究,或积极参与国际ARDS协作网相关研究,为ARDS的循证医学提供更丰富更可靠的证据。
二、1994年AECC诊断标准的缺陷
由于1994年AECC诊断标准简单易行,在国际医学界得到了广泛应用。目前ARDS患者机械通气推荐采用肺保护策略,即包括“小潮气、平台压≤35mmHg、允许性高碳酸血症”,其证据均来源于依据该诊断标准进行的临床研究所得出的结论。该标准能较准确地评估患者预后。临床研究表明,符合AECC标准的ARDS患者与不符合AECC标准的患者相比,前者的预后更差。但是AECC标准从颁布之日起在学术界就争议不止,一些研究结果也表明该标准在临床应用过程中存在不少缺陷。
1.AECC标准未指明“急性起病”的时间范围,是3天还是7天?是7天还是14天?临床判断缺乏一致性。
2.诊断标准中未考虑机械通气参数如PEEP对PaO2/FiO2值的影响,例如,PEEP的应用将通过促进肺复张、增加功能残气量、改善V/Q失调来提高PaO2/FiO2值。假设在PEEP=0cmH2O时PaO2/FiO2为180mmHg,则符合ARDS的诊断标准;但当调整PEEP=10cmH2O而FiO2不变的情况下,PaO2/FiO2升高达250mmHg,则不符合ARDS的诊断标准。除了PEEP之外,FiO2、俯卧位通气、肺复张等均可能影响PaO2/FiO2。由此可见,AECC标准中关于低氧血症的判断不加任何限制条件,可靠性将受到质疑。
3.AECC标准要求排除心源性肺水肿,甚至通过Swan-Ganz导管检查来确定PAWP或PCWP≤18mmHg。但研究表明,危重患者置入Swan-Ganz导管会增加不良事件的发生风险,因此临床已极少实施。
4.ARDS的胸部X线特点是双肺弥漫渗出,因而阅片技术对确定诊断至关重要。一项研究表明,让21名参加机械通气研讨会的专家读取随机抽取28张危重患者(PaO2/FiO2≤300mmHg)的X线胸片,结果显示,不同专家之间的一致率仅有55%,阅片结果与临床诊断的一致率仅有36%~70%,说明阅片者的主观性会显著影响阅片的结论,无疑也会影响临床诊断的准确性。
三、2012年ARDS柏林定义
经过一年的研究和商讨,由欧洲危重症学会、美国胸科学会、美国危重症学会组成的联合委员于2012年5月在JAMA上发表了ARDS的柏林定义(表23-2)。如前所述,1994年的AECC标准存在诸多不严谨之处,而2012年的柏林标准在许多方面进行了细化,目的是使ARDS的诊断标准不仅在临床上容易操作,同时兼具诊断的可靠性及有效性。
1.如前所述,AECC标准并未强调ARDS的高危因素;而柏林标准阐明应识别ARDS已知的高危因素。如果没有,则应注意鉴别心源性肺水肿。
2.AECC标准未指明“急性起病”的时间范围,而柏林标准规定ARDS的起病时间应在1周之内。研究表明,当已知诱因存在时大部分ARDS患者将在72小时发病;而几乎全部患者都会在7天内发病。
3.在柏林标准中ARDS的影像学检查既可以是胸部X线也可以是胸部CT。
表23-2 ARDS的柏林诊断标准
注:*:如果海拔超过1000m,PaO2/FiO2值需用公式校正,校正后PaO2/FiO2=PaO2/FiO2×(当地大气压/760);#:轻度ARDS患者可用无创通气
实际上胸部X线检查尤其是床旁胸片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,而胸部CT有助于更准确地鉴别胸腔积液、大叶性肺炎/肺不张、结节等。
4.《AECC指南》定义ALI的氧合状态为PaO2/FiO2≤300mmHg,ARDS的氧合状态为PaO2/FiO2≤200mmHg,即ARDS是更严重的ALI。但不少医师误以为ALI的氧合状态区间是201mmHg≤PaO2/FiO2≤300mmHg。为避免继续引起歧义,《柏林指南》摒弃了ALI的概念,而根据氧合状态将ARDS分为轻度、中度、重度3个亚组。需要注意的是,在柏林标准中,PEEP/CPAP≥5cmH2O时200mmHg≤PaO2/FiO2≤300mmHg定义为轻度ARDS;而在AECC标准中,上述氧合区间尚不能诊断为ARDS,只能诊断为ALI。所以,柏林标准实际上降低了诊断ARDS的严格程度、扩大了ARDS的诊断范围。
5.考虑到PEEP对PaO2/FiO2值的影响,《柏林指南》在ARDS亚组分类中加入了最低水平的PEEP,所有氧合状态都是在施加至少5cmH2O的PEEP后再进行评价。但是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。临床实践中ARDS患者在机械通气时往往都需要加用>10cmH2O水平的PEEP,在逐渐调整PEEP的过程中,PaO2/FiO2也会发生变化。例如PEEP为5cmH2O时,患者的氧合状态符合中度ARDS;而当PEEP>10cmH2O时,患者的氧合状态就只能诊断轻度ARDS。所以应该对患者的氧合状态进行动态评价。
6.由于肺动脉导管已较少应用,而且心力衰竭和液体负荷过重完全可以与ARDS并存,因此在柏林标准中不再要求测定PAWP或PCWP。非心源性肺水肿即ARDS的诊断和鉴别诊断完全交由临床医师来判断。当没有发现ARDS的显著诱因时,应通过客观检查(如超声心动)来排除心力衰竭。
ARDS的AECC标准和柏林标准,哪个更胜一筹,目前尚无定论,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实其有效性。柏林标准将ARDS进行严重程度的分级可能有助于近期开展针对特定亚组的临床研究,例如重度ARDS患者尽早实施ECMO是否可以改善预后。笔者始终认为,改进ARDS的救治水平和改善ARDS患者的预后,除了依靠高级生命支持技术,更重要的是识别危险因素,并且应按照不同的危险因素分类进行亚组研究。
1.Bernard GR,Artigas A,Brigham KL,et al.The American-European Consensus Conference on ARDS:definitions,mechanisms,relevant outcomes,and clinical trial coordination.Am J RespirCrit Care Med,1994,149:818-824.
2.Raghavendran K,Napolitano LM.Definition of ALI/ARDS.Crit Care Clin,2011,27:429-437.
3.Rubenfeld GD,Granton J,Hudson LD,et al.Interobserver variability in applying a radiographic definition of ARDS.Chest,1999,116:1347-1353.
4.Artagas A,Bernard GR,Carlet J,et al.The American-European Consensus Conference on ARDS.Part 2.Intensive Care Med,1998,24:378-398.
5.Villar J,Perez-Mendez L,Kacmarek RM.Current definitions of acute lung injury and the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do not reflect their true severity and outcome.Intensive Care Med,1998,24:378-398.
6.The ARDS Definition Task Force.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.The Berlin Definition.JAMA,2012,307:E1-E9.
7.Hudson LD,Milberg JA,Anardi D,et al.Clinical risks for development of the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.Am J RespirCrit Care Med,1995,151(2 pt 1):293-301.
8.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.急性肺损伤/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诊断标准(草案).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,2000,23(40):203.
9.急性肺损伤/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诊断和治疗指南(2006).中华实用外科杂志,2007,27(1):1-6.
10.杜斌.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柏林定义:究竟改变了什么?首都医科大学学报,2013,34(2):201-203.
11.侯静静,朱蕾.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诊断的影响因素和判断标准.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,2007,30(8):631-637.
12.俞森洋.对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诊断新标准(柏林定义)的解读和探讨.中国呼吸与危重监护杂志,2013,12(1):1-4.